羌族释比戏:原始宗教与戏剧交融的活态遗产
释比戏是羌族更具代表性的民间戏剧形式,集祭祀礼仪与戏剧表演于一体,主要流传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、汶川、理县及绵阳市北川等羌族聚居区,羌语称“剌喇”或“俞哦”,习称“羌戏”。它是羌族“释比”(巫师)主持祭仪时的产物——释比既是宗教仪式的执行者,也是戏剧表演的核心,因此得名“释比戏”。
一、历史脉络:从祭仪到戏剧的演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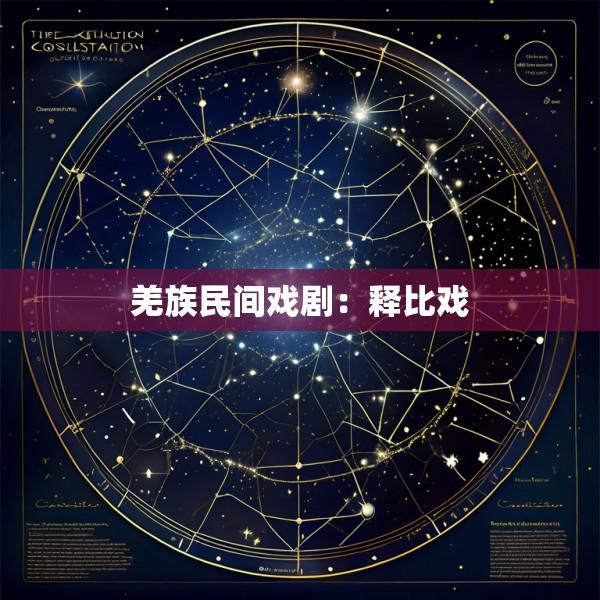
释比戏的形成与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密不可分。羌族自古信奉“万物有灵”,释比作为沟通人与神的中介,其主持的祭祀活动(如祭山、祈雨、驱邪)逐渐融入戏剧元素:将神话传说、历史故事编入唱经,通过说唱、舞蹈、角色扮演增强仪式的感染力。这种“仪式戏剧”的转化,使释比戏成为兼具宗教功能与娱乐价值的民间艺术。《四川傩戏志》明确将其列为“羌族傩戏剧种”,强调其“释比主持、戏剧表演”的核心特征。
二、核心特征:原始古朴的民间戏剧形态
1. 分类与主题:释比戏分为“上坛”“中坛”“下坛”三类。上坛戏叙说神事(如《木姐珠与斗安珠》《羌戈大战》),用于集体祭祀,祈求神灵庇佑;中坛戏反映人事(如《婚嫁》《求雨》),为保佑平安、五谷丰登而演;下坛戏叙说鬼事(如《斗旱魃》《送鬼》),通过法术驱逐邪祟,属于“驱邪仪式”的延伸。
2. 表演特点:释比一人可扮演多个角色(男子、女子、神灵、鬼怪),身段以腿部动作为主(单脚跳跃、左右交替),保留了原始“巫觋礼仪”(如“巫步多禹”,源于大禹治水的传说)。唱腔分“神腔”(酬神祭祀,音律起伏大、节奏慢,句末延音)、说唱体(中坛戏,贴近生活,夹杂夸张道白),无固定剧本,全凭释比口传心授。
3. 演出形态:无固定场所,可在神山、神林、堂屋、草坪甚至婚丧嫁娶的现场表演。道具简单却极具象征意义:羊皮鼓(释比与神沟通的核心法器,击鼓伴随唱经)、盘铃(增强节奏感)、神棍/师刀(法术表演用具)。
三、重要剧目:神话与人间的戏剧表达
1. 《木姐珠与斗安珠》:改编自羌族经典神话,讲述天神之女木姐珠与凡人斗安珠的爱情故事。释比通过说唱展现两人克服困难(如天神阻挠)终成眷属的过程,传递“爱情战胜阻碍”的主题,是释比戏中“神事”与“人事”结合的代表。
2. 《羌戈大战》:反映羌族历史迁徙的重要剧目,讲述羌人从西北南迁至岷江上游,与当地戈基人战斗,最终在天神帮助下定居的故事。剧中融入“羌人坚韧不拔”的民族精神,是释比戏中“集体记忆”的载体。
3. 《婚嫁》:中坛戏的经典,以“新郎新娘成亲”为背景,释比扮演新人、媒人等角色,通过一问一答、插科打诨(如调侃新郎的紧张)展现婚俗细节,语言幽默,贴近生活,是羌族“婚嫁文化”的戏剧化呈现。
4. 《斗旱魃》:下坛戏的代表,讲述旱魃作祟导致干旱,释比带领村民捉拿旱魃(藏匿于山林中)的过程。剧中“捉旱魃”的仪式与戏剧表演结合,既驱邪又娱乐,体现了羌族“敬畏自然”的生存智慧。
四、传承现状:亟待保护的活态遗产
释比戏的传承主要靠释比家族“口传心授”,但随着老释比年事已高(如汶川93岁释比余明海),年轻一代学习意愿薄弱,传承人数量锐减(茂县、汶川等地仅余数十名释比)。现代娱乐方式的冲击、羌区人口外流等因素,使释比戏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。近年来,理县蒲溪乡通过“夬儒节”(省级非遗)展示释比戏,与学者合作开展抢救性记录(如录制释比唱经、整理剧目),但仍需更多措施保护这一“羌族文化的活化石”。
